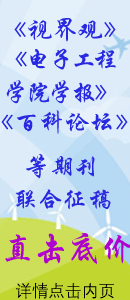
论文摘要:从2007年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小说还是童诗、童话、散文,都自然地显现出儿童文学民族性的丰富和美丽,而儿童文学民族性又自然地与当代性、儿童性相交融。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发展到现在,虽然仍处于弱势,却面临着新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机。可以看到,来自各方面的鼓励和倡导,已经和正在显示出对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整体促进。
论文关键词:民族儿童文学;文学创作;创作理念;创作特色;民族性;当代性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发展到现在,虽然仍处于弱势,却面临着新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机,有3件事需要特别提到: 1.继满族女作家王立春的诗集《骑扁马的扁人》获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之后,蒙古族青年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长篇小说《黑焰》获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2.国内最具实力、最有影响的几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已在密切关注近年崭露头角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并及时地出版他们的作品,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连续出版了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中短篇小说集《重返草原》、长篇小说《鬼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接力出版社也出版了民族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3.由中国作家协会、共青团中央联合主办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参会代表中,经常写儿童文学的少数民族作家有3人(蒙古族黑鹤、土族张怀存、满族于晓威),有时写一点少年题材作品的2人(东乡族丁一容、藏族扎西达娃)。可以看到,来自各方面的鼓励和倡导,已经和正在显示出对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整体促进。
民族儿童小说,一直是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最重要的部分。民族作家们在抒写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生存状态时,总是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那一民族在那一年代、那一地区的社会风貌、地域风情,总是会凸现出那一民族儿童迥异于别民族儿童的内在的、情性的种种元素,从而使儿童文学民族性凸现出来。所以,民族儿童小说虽数量不多,作品中的民族少儿形象却因其鲜明的民族色彩而棱角:9-明、性格独具。如维吾尔族作家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的中篇儿童小说《心山》,写了3个年龄相仿、向往美好却家境各异、性格相殊的维吾尔族少年:一个是在城里上学,喜欢乡村的淳朴、安宁而来奶奶家度暑假的,白净、内向,12岁的伊力多斯;一个是长年与爷爷作伴,有能耐、有主见,却又因照顾爷爷,一人干活而没有上学的,矮小、聪明,10岁的米拉吾西;另一个也是12岁,却个儿最高、力气最大、懂事最多、干活最行,只因父母离异无人管束而有了一些坏习惯的吐来克皮特。这3个少年因为被村-T"里流传的“心山”的传说所吸引,因为被传说中用鲜血挽救楼兰孩子的拜格库勒拜格和使心脏变成了“心山”的“漂亮母亲”所感动,竞自作主张,去寻觅那座天天被日头映照得像是刚被掏出来的心一样鲜红的“心山”。整部作品都在描述他们走向“心山”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以及他们面对困境的表现:当他们走进无边无岸的沙漠,米拉吾西想到的就是让伊力多斯用小木棍在沙地上写字给他看;当黑夜带着突如其来的饥饿和孤寂、带着渗进骨髓的寒冷和恐怖压过来,吐来克皮特给他俩讲鸽子蛋、烤鸽子,还挖出3个御寒的沙坑让同伴们睡下;当沙丘的另一端有一条大沙蜥在吞吃小沙蜥时,伊力多斯最先发现,吓得哭了,吐来克皮特却把原因讲给他俩听,又用鞋子打死了正在爬过来的毒蝎;当狂暴的沙尘从远处刮过来,3个同伴紧紧抓住彼此的手去寻找可以避风的地方,可是,狂风像吹飞篷似的,使他们消失在沙暴里。这3个维吾尔少年形象,不仅丰富了中华儿童文学的人物画廊,也使我们在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新发展的探究中作更深入的思索和思考,民族心理素质不是一个空泛、抽象的概念,探究它的发展、变化,主要地、也必然地在新一代民族少儿形象的刻画中展示出来。从《心山》中这3个同民族、同家乡的维吾尔少年形象看,当下的社会现实、生活环境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具体、不同的影响,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崇拜民族英雄的情结,更有着对知识的渴求、对展示自身才能和创造奇迹的渴望,以及对于来自他人的尊重和关怀的渴盼。作家对他们的心境、言语、行动的细心而真实的描写、刻画,具体地揭示出民族心理素质新发展的丰富内涵。小说中,对遥远大漠的空旷、死寂的形象描述与尽情渲染,对猛烈沙暴中狂风呼啸的震耳欲聋、黄沙漫天的天昏地暗、沙丘起伏的瞬间变动的有声有色的比喻式的叙述,令读者身临其境而感同身受。这样的描写和叙述,绝不能只用艺术技巧来概括,不仅只是语言运用的高超,可以说,不是生长在这一民族地区的本民族作家是绝对写不出来的。何况,透过民族作家的这些描写与叙述,读者了解到的,也不只是那里的自然环境、地域状况,更是关于这里人们或已经远离或不愿离开或难以离去而形成的错综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状态,其中当然包括了思想观念、道德情操等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显然,一位民族作家,如果没有本民族生活的深厚积累,没有热爱本民族人、尤其是热爱本民族儿童的真挚感情,是万万写不到这个程度的。而说到底,通过民族儿童形象的刻画,揭示民族心理素质的新发展,正是儿童文学民族性最鲜明的体现。可以看到,儿童文学民族性,正是民族作家全身心地体验、感受、反映民族儿童的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结果。
另一篇柯尔克族的儿童短篇小说《三条腿的野山羊》,与《心山》异曲同工。小说集中刻画了一个居住在高山脚下,父亲至今仍以猎捕为生而自己心理却非常同情、爱怜这些生长在山里的动物的柯尔克孜族少年努力别克的形象。已经上了学的努尔别克是一个学习用功、心地善良的好少年,却经常因为父亲带着他上山去查看猎夹而旷课,又因为猎夹里夹住了野山羊而与它们一起承受痛苦。但是,在那僻远闭塞的小山村里,父亲只是要让他成为一个像样的猎人而从来不把他们的学习放在心上。小努尔别克无法违抗父亲意志,更无力改变猎人的生活,但是,猎夹中夹着一条血淋淋的野山羊的腿,那只三条腿的野山羊正在远处守看被猎夹夹住的小山羊的情景,以及三条腿野山羊的惨叫和小山羊挣扎时的嚎叫,使他心灵震颤,也使他在父亲病后自己上山查看猎夹时放走了那只已被夹住的野山羊。努尔别克的这一举动当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他的本性和真心的表现,会激起各民族小读者的共鸣,也会引起人们关于民族地区社会变革、生活变动的思索和思考。
作者着力地描写努尔别克因父亲的强迫,“吃力地走在后面”,“胸闷躁热,双腿发软,浑身是汗”的情状,描述他因同学询问缺课原因而“心里像是什么东西堵着似的火烧火燎的”情境,描叙天气骤变、风雪交加之中,“他运用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本事,将大山羊翻倒在地,把套在猎物腿上的绳索用刀割开而后使野山羊自由的情形。努尔别克的个性正是在这样的情节里展示得清晰而生动,作品中生态保护的题旨也就这样在物质的、精神的层面同时显现出来。相比《心山》,这篇作品的情节、人物都比较简单,难得的是,这篇小说的作者——柯尔克孜族的阿依别尔地·阿克骄勒,是一名在校的高中学生。他远离家乡却坚持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作品中渗透了对家乡、对民族、对本民族中幼小儿童的深爱之情,虽结构极单纯,内涵却丰富,而且,这种丰富,只有用他特有的心灵去感觉,才可能一一地揭示出来。
但是,这两篇小说的结局却都是活泼少年的死亡,他们或死于因寻觅“心山”而遭遇沙暴,或死于因解救猎物而雪中迷路。可爱少年的可悲命运,使作品具有了巨大的情感上的冲击力,自然灾难固然难以抗拒,但为什么新世纪的民族少年仍然生存、生活在如此落后、封闭的现实环境之中?为什么这些少年的父母的言行都丢弃了本民族原有的淳朴并对孩子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又为什么少年与长者之间竞无法沟通?不过,从民族儿童小说来说,死亡的结局实在是太沉重了。也许这是作者认为悲剧比喜剧、正剧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也许这样的表现会让人们对民族心理素质的变化、发展、提升有更深刻的认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近期民族儿童小说的现实性更为强烈,小说中不同民族的少儿形象都不仅有鲜明的个性,更体现出当代性与儿童文学民族性的浑然一体。
换一个角度看,又可以看到民族作家们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念在发展,面对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各民族儿童,民族儿童小说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并不有意地要回避什么或是掩盖什么。因此,这些作品常常在流露出对民族儿童的天然感情的同时,彰显出一种明朗的批判精神。又如,瑶族冯昱的《栖息在树梢上的女娃》。作家以悬疑的方式展开某一民族地区重大社会问题的故事,小说的主要人物就是栖息在树梢上的女娃,女娃在小说结尾时从树上摔下死了,小说的故事是在她死去之前的追忆和叙述中铺陈开来的。女娃10岁时读完三年级就失学了,父亲让她采割松油挣钱,于是她就成了村里年龄最小的割油娃,是那个年代里受苦最深的民族儿童的典型。作家用一些常常被人忽略的细节写活了这个瑶族女童形象,并由此触及到山寨的贫困、滞后,村官的腐败、丑恶,百姓的愚昧、屈辱,令读者产生震惊以至惊悚的感觉,从而使这个民族儿童形象更加凸现,也让人们不得不对这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民族儿童的遭遇、命运作仔细的、深入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这篇作品所塑造的民族儿童形象才显示出了它在儿童文学意义上的独特价值,也显示出了一位民族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有的民族作家并不是要专门地创作儿童小说,这一点,从作品的题目就可以明显地表示出来。但,他们却在作品中写出了活泼泼的、有血有肉的民族少儿人物形象,写出了特定年代、特定地域中特定民族少年儿童的生活情境和心理状态,写出了能够打动人感染人的童心美和人性美。如裕固族青年作家苏柯静想的《白骆驼》、侗族北洛的《阿罗》、蒙古族瓦·萨仁高娃的《骑枣骝马的赫儒布叔叔》。
《白骆驼》以清新优美的叙述、神秘的历史和现实氛围,写出一个裕固族少年苏柯尔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生经历:拉骆驼,进闹市,遇盗贼,救白驼,识诡计,捉匪首,当干部。让读者了解历史、时代与民族儿童命运的复杂关系,认识人性的深邃、正义的高贵。《阿罗》与《骑枣骝马的赫儒布叔叔》,题目上写的都是大人的名字,作品里面也都写大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但,令人难忘的却是阿罗的女儿、侗家女娃二丫这个形象。二丫患血癌,却因卖糖货叔叔喜欢她,送她小喇叭,给她扎花,为她吹口琴,像对女儿一样待她,使二丫总是高兴得像个公主似的,笑得很灿烂。村里人在背后议论阿罗,卖糖货的也很久没来,二丫在病中一直想着卖糖货的叔叔。卖糖货的再来时已是秋天,二丫死了,留下的是二丫的美丽童心和真挚爱心。后一篇中,那个生下来不足百天就失去了父亲,在偏僻山野上长大的蒙古族小男孩“我”因母亲的辛劳和赫儒布叔叔的关爱而能走进学校,走进城市。“我”是一个懂得感恩、懂得进取的少年,只是无法为母亲拂去心头的阴影,抹平心灵的创伤。两篇作品都有其情感上、认识上的价值。
也有的民族作家通过对某一年代某一地区某一少年形象的刻画,表现一段历史。作品里少年形象的族别似乎不再重要,社会变革、生活变动的各种因素被强调地展示,某些过去未在民族儿童小说中被注意的主题得到更深开掘。如侗族佘达忠的《少年良子的成长》、满族赵大年的《属鸡的女孩》。这样的作品,作为民族作家创作的少年题材小说的一种类型,值得关注和研究。
长篇小说中,蒙古族青年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鬼狗》,延续了他的创作风格。小说写一只名字叫“鬼”,却一身纯白像传说中的雪狼似的巨猛獒犬:前半部着力地描述鬼狗的野性、蛮性,也由此写到拜金主义潮流中人性的扭曲与泯灭;后半部则有意地写鬼狗在内蒙古大草原上遇到蒙古族小男孩阿尔斯楞的种种情景,用诗性的语言抒写阿尔斯楞对鬼狗的关切与深爱,深情地描绘鬼狗对阿尔斯楞的温情与顺从。那段写阿尔斯楞与鬼狗在草原上互相追逐游戏的场面,激烈而欢快,紧张而舒缓,不仅使作品具有了象征的、哲理的意义,更使阿尔斯楞身上的蒙古民族心理素质表现得淋漓尽致。阿尔斯楞,虽然是在小说后半部才出现,却是作家钟爱的草原少年形象,作家的独到在于他剔除了当代社会中功利对人的压折,将这一少年形象置于空茫的天地之间,从而把一个普通的蒙古族少年形象提升到形而上高度,使其具有了象征的、哲理的意义。
童诗和童话是民族民间儿童文学中最兴盛的两个门类,但在一段时间里民族作家们却很少涉及。2007年,这方面的创作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第一,瑶族诗人唐德亮的童话诗《羊,或者狼》被评为《儿童文学》月刊“10首魅力诗歌”之一,唐德亮获“全国十大魅力诗人”称号。当年,他的童话诗《天堂动物后悔座谈会》、《太阳是一枚金蛋》、《长不高的树》,以及描写儿童生活和心情的童诗《童年的梦》(三首)、《童韵》(二首)等又连续发表在广东及其他省的报刊上。第二,满族作家佟希仁的五首儿歌《蝴蝶落》、《海浪花》、《吓一跳》、《小雪花》、《小狗喝酒》被收入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快乐健康儿歌丛书》。第三,满族作家肇夕的童话集《绕树一小圈儿》、佟希仁的幼儿童话集《彩彩坐云端》相继出版。应该说,这是民族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好兆头。
唐德亮的《羊,或者狼》,8小节,106行,排比的句式,铿锵的节律,包含着丰富的幻想、精密的布局,折射着错综的现实、复杂的生活。虽然,诗中隐匿的意思、意味,不同民族、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会有不完全相同的领会和领悟,但,羊与狼这样的传统童话题材和巧妙的现代手法,琅琅上口的语言和曲折有致的情节,却使作品具有了最适应儿童审美心理的趣味性与启发性,并且使民族地域的色彩很自然地消融其中。那首《天堂动物后悔座谈会》,更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又隐隐地透露着生长在山林乡野的民族儿童所特有的生态保护的紧迫感。诗虽小,串连成一组,独具韵味。
满族作家佟希仁为幼儿创作的儿歌、童话都漫溢着情和趣,又都深藏着爱和美。他的作品既自然地展现东北大地的景色,又真切地透露着满族人喜勤快压懒惰、重诚信斥虚伪的情操。另一位满族女作家肇夕,把童话写得空灵飘逸,读完那本《绕树一小圈儿》里的一个个童话,感觉这些童话境界里的奥秘都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说,但,读完每一段又都会有一个画面在你眼前定格。肇夕的高明之处,在于这些画面的延续、连接中,使童话的情节或延伸或跳跃,充满着幻想的超性和幽默感。比如,写一粒外出执行任务而迷路的油菜籽,先是遇到了风雪交加的特冷的冬天,继而爬到了一个打更人的窗子外头,正遇上打更人晒种子的日子,接着,得到了蚂蚁王国的帮助,爬到了窗台上,由于北方的大部分种子没有见过油菜,惊动了筐箩里所有的种子,更夫最后把这粒他不认得的小小油菜籽种在窗台下的空地上,从此,北方也开了油菜花(《油菜籽历险记》)。故事场景虽令人称奇,作家却写得随意自如、热情洋溢、天真烂漫的童情洇透了每一个画面,生命的意趣、生活的意味、生存的意义,俱在其中;而且清新的地域气息扑面而来,不鄙弃细微、不忽视细小的民族文化中的传统意识在现代童话的诠释中更加光大。
另一篇《呱呱呱》,直接描述住在一个满族皇帝宫殿里的乌鸦公主的生活。作家说她“是一只黑色的小鸟”,却“有点儿像个小男生”。她不循规蹈矩,倒爱胡思乱想,爱跟小宫女搭话儿,爱捡拾掉在地上的谷粒、;当父皇和母后都已故去,其他的公主都已老去,她竟把以前从宫女、大臣那里听来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乌鸦公主日记,又编成一本乌鸦公主地图集。肇夕这种似传统非传统、似现代非现代的童话方式不仅令人感到新鲜、新颖,产生一种艺术上的陌生感,而更主要的是从中看到她对于民族民间文化的借鉴和汲取。当然,她并不拘限于本民族,也广泛涉及西方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化,这一点,从《狐狸镇》、《粉脸狮子》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来。而《呱呱呱》的中心内容应该主要显现在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审视和批判,其间也糅进了对当下一些社会现象的体察和思考。肇夕的童话创作进一步揭示出儿童文学民族性的丰富和发展:今天,在这个全球化了的时代里,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真实文化背景已经较过去开阔广泛得多,而不再仅仅是自我民族的;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也不再仅仅关注民族特色的外部特征,而把作家自己的思想、艺术深入到本民族文化根系中。
此外,也有作家尝试着写童话式小说。如傣族黄国平的《猫、狗、人》,其幻想与现实交织,诗情与哲理交融;写猫的清高、狗的谄媚,写小孩的善良、大人的自私;有点传奇的色彩,有着生动的意蕴;引发读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而作家运用的展示人、猫心理独白的艺术手段,也在借鉴中有所创新。
也有的民族作家的诗歌不是有意为儿童写的,却很适合儿童诵读。如回族沈沉的《刘胡兰》,满族高若虹的《风中的草》,瑶族李祥红的《瑶家吊脚楼》,维吾尔族阿布利孜·奥斯曼的《童年的梦》等。
民族作家为儿童写的散文很少。但,很少的几篇却都有着民族儿童独特的视界,有着他们稚真的情思。如哈尼族陈强的《背柴》,写11岁的“我”与8岁的弟弟放学以后去柴山,赶在太阳落山前急急忙忙地砍柴,又在山风的呜呜嚎叫中,在新月的幽幽光照下忙忙慌慌地回家。一路上,弟弟背不动了,“我”就把弟弟背上的柴禾抽出几根放到自己背着的柴禾里;弟弟害怕了,他就让弟弟走前,自己走后,又把弟弟的柴禾抽几根放进自己的柴捆。文字很简洁,内容也单纯,却写出了那一年代哈尼人生活的艰难、哈尼儿童童年的苦涩。作家所描写的山村的闭塞、山路的荒凉,又呈现出那一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散发出那里所特有的生活气息,从而形成一种难忘的情感氛围。另一篇《萍姐》,写儿时在村里的小伙伴萍姐怎样领大家做游戏唱儿歌,到邻村看电影,又怎样在风雨中用自己瘦弱的身躯保护她的弟弟和“我”,也令人感受到童情的稚真和珍贵。这样的作品,篇幅虽小,终因其情感真忱,个性凸现,贴近心灵,而有一种撼人心弦的力量。
有的民族作家总是满怀深情地叙述童年记忆,如满族的西风。他的《走近村庄》写10来岁时上碾房推碾磨面,读初中后到水井边担水,在摇篮旁看护弟妹,以及小时候穿着母亲手工纺成、缝制的衣服,戴着红肚兜儿的情景,让当下的民族儿童了解本民族往昔的生活风习,让往昔的岁月被心灵的烛光照亮。另一位满族作者高维生的《冬天的记忆》,也是写印在心灵中的童年生活,但作者是以童年的口吻来叙述的,更富儿童情趣,更有童稚情味,精妙的文字中更具一种民族、地域文化的气韵。这类作品还有哈萨克族阿吾力汗·哈里的《燕子到我家做了窝》,蒙古族萧童的《黄瓜架下的温馨》等。可以说,这些作品连成了以往岁月中各民族儿童生活的画卷,是由各民族儿童的童年构成的形象的历史。
也有的民族作家注意引导儿童认识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杰出人物。如彝族作家张昆华的《聂耳绝唱》,从坐落在昆明市甬道街的聂耳故居,写出聂耳的音乐创作、革命人生,写到聂耳的墓地和他的永垂不朽。聂耳的母亲是傣族,母亲从家乡寄给在日本的聂耳的缅桂花,一直保存在聂耳生前最心爱的那把小提琴的琴盒里,虽干枯却芳香。我们从中能读出聂耳的民族情怀、故乡情结,作家的敬仰之睛、缅怀之睛。
散文崇尚真情,与民族儿童最是心灵相通。儿童文学民族性在民族儿童散文中体现得真切而具体。
从2007年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小说还是童诗、童话、散文,都自然地显现出儿童文学民族性的丰富和美丽,而儿童文学民族性又自然地与当代性、儿童性相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