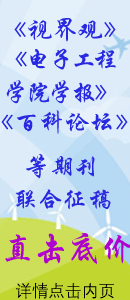
一、“人文主义”与“新人文主义”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需要作一点说明:目前国内研究者多称白璧德学说为“新人文主义”,并多称白氏为“新人文主义批评大师”,但实际上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新人文主义”这一提法或许并不完全对应。
首先,白璧德在陈述自己思想的时候,般均采用“人文主义”这一术语,而从未自称其学说为“新人文主义”。事实上,他不但极少使用“新人文主义”这一概念,且该词一旦使用,辄呈贬义。须知,白璧德素来喜“旧”而厌“新”(详见本文第三节“二元论”部分的论述),他不可能将自己的学说冠以“新”字;同时,根据哈佛1933年10月3日会议中《关于欧文·白璧德的生平和贡献》(Minute on theLife and Services of Professor Irving Babbitt)一文的记录,“他[白璧德]常说自己所要表达的并非新鲜事物,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学说被称作‘新人文主义’。对他而言,并无所谓的‘新人文主义’,而只有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亘古不变的对立……”——这一记述或可说明一些问题。
此外,在美国当时的思想界,白璧德的这一学说始终被称作“人文主义”,直至上世纪20年代末,随着白璧德、穆尔(Paul ElmerMore,白璧德的终生挚友、“新人文主义”运动的又一领袖)等人的学生纷纷投入白、穆二人之“人文主义”学说的文学阐释实践中来,文学批评界才出现了“新人文主义”这一提法。伴随着“新人文主义”运动的日渐高涨,人们有时不免会将二者混为一谈,如某些西方研究者便顺理成章地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称作“文学人文主义”(literary humanism),这一误解正说明有关研究者多少混淆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与“新人文主义者”们的文学阐释实践活动。须知,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涉及到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史、政治学、哲学、佛学等各个领域,而不仅限于文学这一个方面;而他(以及穆尔)的学生们(即真正的“新人文主义者”们)多是学院中的文学教授,其研究工作往往是根据“人文主义”思想而展歼的文学阐释实践,这些实践活动在上世纪20年代蔚然成风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称“新人文主义运动”,与这一运动的思想基础——“人文主义”——自是有所区别、
此后曾有研究者著文澄清这种普遍的认识上的混淆,如格罗瑟林曾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区分为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哲学的“人文主义”(humansim as a philosophy),这以“人文主义”的两大创建者——白璧德与穆尔——的哲学研究为主;而另外一层则是作为运动的“人文主义”(humansim as a movement),运动的参与者们大多是白穆二人的学生,作为其追随者,他们并不关心这一学说的哲学根基,而是直接将这些论断运用到“文学批评”(literarycriticism)领域中去。也就是说,前者不仅限于“文学”,故不可单纯地称作“文学人文主义”,而后者便是所谓的“新人文主义”运动,作为“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一个运动,或可与“文学人文主义”的称谓拉上干系、从而,我们可以说白璧德是“新人文主义”的奠基人,但是如果进而讨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这种说法便可能会导致某种混淆
在中国现有的大量相关研究中,白璧德的思想一般均会被指称为“新人文主义”,但需要注意的是,五四时期宣扬自璧德学说的大本营——《学衡》——却几乎从未将这一学说称为“新人文主义”,而是始终称之为“人文主义”。直至1931年3月,在第74期《学衡》张荫麟短篇译文《白璧德论班达与法国思想》吴宓所作的按语中,才第一次出现了“可见白璧德先生新人文主义之夫旨”这种表述,这也是唯一的一个特例。看来,就白璧德学说的相关阐释史而言,并非是第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么,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在中国一变而成为“新人文主义”的呢?——这一问题将留待后文加以解决,以下我们且回到本文主题,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探究竟。
二、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定义简述
人文学者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认为,对于人文主义及相关词汇,“没有人能够成功地作出别人也满意的定义”,他本人不拟将人文主义当作一种思想派别或哲学学说,而是当作“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并统称之为“人文主义传统”。可惜布氏这部1984年完成、1985年出版的著作未能关注到白璧德的学说,虽然白璧德井不一定成功地给出了“别人也满意的定义”,但是,白璧德那种来自其渊博学识、态度鲜明而略带独断论痕迹的对于“人文主义”概念的辨析与厘清,极大地丰富了这个关键词的内涵,他的思想亦足以成为整个人文主义传统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在白璧德看来,厘清“人文主义”一词的涵义,最重要的是辨明“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区别。“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区别还涉及到“人律”(1awfor man)与“物律”(Law for thing)、“一”(theOne)与“多”(the Many),以及“博放时期”(era of expansion)与“精约时期”(era ofconcentrati’on)等若干组对立的概念。这些概念分为两个阵营,一方为与“人文主义”相联系的“人律”、“一”和“精约”等概念,另一方为与“人道主义”相联系的“物律”、“多”和“博放”诸概念,各阵营内部之概念的内涵彼此重叠,往往一个概念的出现,意味着其他相关概念的同时在场。
白璧德首先探询了“人文主义”一词的拉丁词源humanus,这个词最初意味着“信条”(doctrine)与“规训”(discipline),且它“并不适应于芸芸大众,而只适合于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人”,即它“是贵族式的”(aristocratic)而非“平民式的”(democratic),而人道主义者则对“全人类”富有“博大”的“同情心”,如今人们却多将“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相对于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的关怀对象更具“选择性”,关注的是“个体的完善”,而非“全人类都得到提高的那种伟大蓝图”,他坚持“同情”(sympathy)需用“选择”(selection)加以调节,因此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便是在“同情”与“选择”之间保持着“正当的平衡”(a just balance)。
但是,尽管“人文主义”一词最初意味着“信条与规训”,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对于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而言,“人文主义”却意味着对一切规训的反抗,“是一种从中世纪的极端走到另一极端的疯狂反弹”,然而到文艺复兴后期,其主要趋势又远离了那种欣赏“自由扩张” (a free expansion)的“人文主义”,转向了具有最高程度的规训与选择的“人文主义”。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认识与需要,人们在不同时代对于“人文主义”产生了不同的定义,于是便导致了“人文主义”概念的含混不清。通过梳理这一含混不清的“人文主义”概念,白璧德向我们揭示出其中蕴藏着的一个清晰的历史发展模式:“人文主义”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趋势,这两种趋势随着不同时代的不同要求交替产生,甚至在同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中,亦分两个时期呈现出来。例如,在文艺复兴的第一个时期,占据主流的是一种解放运动,这便是“第一个伟大的现代扩张时期”,是“对个人主义的第一次促进”,但是,当“无政府主义的自我张扬和放纵”的“博放时期”对于社会似乎已经构成威胁的时候,社会便会开始对个体产生反动,于是在文艺复兴的第二个时期,强调规训与选择的“精约时期”便随之而来。这两种时期交替出现,不断对前一时代形成反拨,起到补弊救偏的作用。
白璧德还进一步指出,尽管“精约时期”与“博放时期”互为反动,但这两种对立的趋势实际上存在着“目标的潜在统一”:“人文主义”根据时代的不同,或侧重于“一”,强调规训与选择,内敛自制的原理(即“人律”)得以彰显;或侧重于“多”,支持自由扩张,大力促进个人主义,表现为自我的张扬与放纵(即“人律”失而“物律”显)。过度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走向极端的“多”)和过度的“超自然主义”(supernaturalism)(走向极端的“一”)都会破坏这种平衡,完全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彻底的灭亡,例如古印度因过分强调“一”而毁灭。反之古希腊因泛滥于“多”而衰落。从而,“适度的法则”(the lawof measure)才是最高的人生法则,我们强调“人律”而反对“物律”,就是要充分重视并运用精神上收敛集中的原理,使个人人格日臻完善(perfection),造就“完人”(the completeman)。人注定片面,而人之所以成为人文的,就在于他能战胜自身本性中的这个命定之事。人文的心智就是要在“一”和“多”之间保持最佳的平衡。事实上,人文主义者只能在极度的“同情”(sympathy)和极度的“规训”(discipline)与“选择”(selection)之间,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摸索平衡的支点,并根据调和这两个极端之比例的程度而变得“人文”——这就是“人文主义”的真谛。因此,上述两种趋势的目标就是一致的,即都在于“造就完善的人”,只不过一方是希望通过“扩张”、而另一方是希望通过“集中”来达到这一目的罢了。
通过运用这些丰富的二元对立项,白璧德给出了一种阴阳运式的历史观,在这个模式下,每一个时代都是对前一时代的否定与扬弃。尽管白璧德本人对于一切形式的历史哲学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但从其精确不移的“二元论”式的历史发展模式看来,特别是其中对于“潜在统一”之“目标”的强调,他的历史观仍不免带了一丝历史哲学的痕迹,这深深地影响到白璧德此后所有著作的品格,不论它们分别处理的主题有何不同,其中所贯穿的基本概念则完全一致。
三、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
白璧德一生有著作八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Essays in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1908);《新拉奥孔》(The New Laocoon:An Essay on the Confusion of theArts,1910);《法国现代批评大师们》(The Masters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1912);《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1919);《民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1924);《论创造性及其他》(On Being Creative and Other Essays,1932);《法句经》(The Dhamrrmpnda:Translatedfrom the Pali with an Essay an Buddha and theOccident,1936);《西班牙性格及其他》(SpanishCharacter and Other Essays,1940)。这些著述涉及内容极为丰富,难以全方位加以阐述,不过其中的核心概念则一以贯之:1 一个基本点——“内在制约”;2 “二元论”;3 “存在的三个等级”。以下试分别论之。
1 一个基本点——“内在制约” (inner check)
“内在制约”(inner check)是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最核心的概念。白璧德的八部著作表现为这一概念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展开,分别论证了“内在制约”在教育、艺术、文学、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如何实现并发挥作用。那么,何谓“内在制约”?由于这个概念(以及其他核心概念)在白璧德语汇中是逐渐成形的,我们不妨先就该词的生成过程作一了解。
该词在《新拉奥孔》一书中首次出现,但仅出现过这一次,见白璧德引述爱默生语:“东方人将神(God)本身定义为那种‘内在制约’”,并指出“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几乎在所有真正的宗教书籍中都可找到这一观念”。
“内在制约”一词虽然在白氏奠基之作《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中还未出现,但该书第一章“什么是人权主义?”(What isHumanism)已经指出,“人文主义”一词最初意味着“信条与规训”,今人如果不像古人那样给自己套上信条或规训的枷锁,至少也必须内在地服从某种高于“一般自我”(the ordinaryself)的东西,不论他把这东西叫作“上帝”,还是像远东地区的人那样称为“更高的自我”(higher self),或者干脆就叫“法”(the law)。假如没有这种内在的限制原则,人类只会在各种极端之间剧烈摇摆,只有遵守“核心准则的管束”,在“一”和“多”之间保持最佳的平衡,人的心智才能保持健全。由此可见,书中“内在制约”概念之基本意涵已露端倪。
这一概念在此后的《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定义与拓展。“内在制约”是一种永恒的、或云“伦理的”元素,是人类经验的“共同核心” (common center),对于“放纵的欲望”(expansive desire)呈现为一种“制止的力量”,是相对于“生命冲动”(vitalimpulse)而言的“生命制控”(vital control),是相对于“道德上的懒惰”(morm laziness)的一种“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同时还是否定原则(no-principle)对于肯定原则(yes-principle)施行的一种否决权力(vetopower)。从本书开始,该词作为白璧德最常使用的核心词汇之一,在以后出版的《民主与领袖》、《论创造性及其他》、《西班牙性格及其他》等书中频繁出现,呈现出多种表述方式,如“内在控制”(inner control),以及“内在控制原理”(inner principle 0f control)等,并逐渐统摄了更多的二元对立项,由此涵义不断扩大而日趋清晰丰满。
以上列举的大量二元对立项,既是说明“内在制约”概念的工具,又是“内在制约”概念自身的内容。从这个概念本身来看,“内在”(inner)预设了“外在”(outer)的维度,“制约”(check)要求“制约物”与“被制约物”同时并存,二元对立成为“内在制约”概念的内在规定性,无处不在,伴随始终,我们必须结合下一部分关于“二元论”的讨论,才能更好地解释这个概念。
2 “二元论”(dualism)
白璧德使用了多种不同的词汇表示“二元”状态:或用“二元性”(duality),或用更具哲学意味的“二元论”(dualism),或直接以“对立”(opposmon)名之,有时还会使用“二元的”(dual)或“二元性的”(dualistic)这类形容词,有时索性使用更为生动的“裂隙”(cleft)一词,最常见的便是“二元论”一词。
同样地,有关“二元”的提法虽然在其首部著作中并未明确作为概念提出,但其基本意涵已经呈现,如《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首页题铭以爱默生的诗句,说明“人律”与“物律”彼此分立,无法调和,“人律”事关人类文化,而“物律”与人类物质生活密切相关。白璧德认为小而专精的学院(college)是文化存亡续绝的所在,提出应支持小学院以对抗当时愈演愈烈的一味追求建设规模的综合性大学(umverslty)的潮流。。在《新拉奥孔》一书中,白璧德复根据古典规范批判了文学艺术“样式的混淆”(m61ange des genres),“样式的混淆”作为与古典规范相对立的一元,本身又分前后二种,前一种为“伪古典主义时期的混乱”,莱辛曾针对这一时期的混乱作出了诗与造型艺术的区分,后一种则为“浪漫主义时期的混乱”,白璧德对这一时期纷繁的文艺潮流进行了清理与批判。
“二元论”概念最早见于《西班牙性格及其他》一书“论帕斯卡”(Pascal)一文,其中出现了“人之高上及卑下自我之间真正的二元论” (the actual dualism between the higher andlower self of man)这一说法。该书虽系白璧德身后(1940年)出版,但出现“二元论”概念的“论帕斯卡”一文早在1910年便已发表,后由白璧德门人弟子收录于该论文集。此外,据该书前言所说,关于帕斯卡等人的文章是白璧德就这些意义重大的人物所写的最为详实丰富的论文,尤其帕斯卡还是白璧德开设课程中长期以来讨论的主题。也就是说,这一提法很可能伴随有关帕斯卡的课程,在更早的时候就已提出,只是直至1910年方形诸笔端。
在白氏名著《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中,“二元”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并呈多种表达方式,如导言部分给出了“人性的二元性”(theduality of human nature)的提法,正文部分出现了“人类精神之二元论”(the dualism of humanspmt)的说法,后文使用了“dual”这一形容词进一步解说这“二元”何谓:就“自我”(self)一词而言,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dual being),其中一元为“伦理自我”(ethicalself),与他人共有,另外一元为个人的“性情自我”(temperamental self),后者应置于前者的管辖之下,等等。
至白氏最后一部专著《民主与领袖》,该词发展出了又一组二元对立项:“人文主义”基于对“内在生活”(inner life)的认识,而“内在生活”便是“精神法则”与“肢体法则”之间的“对立”(the opposition between a law ofthe spirit and a law of the members)。在论文集《论创造性及其他》导言中,白璧德进一步郑重强调,人文主义者由于认识到人的内心有一个能够实施“控制”(control)的“自我”,并有另一个需要“控制”的“自我”,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则必然是“二元论的”(dualistic)。至此白璧德明确道出了自己的“二元论”的“人文主义”人生观。
同时,白璧德对一切非“二元论”的人生观均持否定态度:早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第一章第三节关于“一”与“多”之哲学命题的讨论中,白璧德已提出必须在“一”与“多”之间保持最佳的平衡,既反对走向极端的“多元论”(pluralism),又反对走向极端的“一元论” (monism),而应遵守“适度的法则”,这为日后制衡“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二元论”概念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在《新拉奥孔》第七章第二节中,白璧德则特别针对“一元论”明确提出了批判:“一元论”不过是人们由于自己的懒惰、片面,不愿意调节现实中多样而彼此冲突的各个方面而造出的一个好听的说法而已。
白璧德的“二元论”就其本身而育涉及两个层面:相对于外部的物质生活,存在一种对立的“内在生活”,此为“外在”与“内在”二元;“内在生活”又表现为“高上自我”对“卑下自我”之制约,此为“制约”与“被制”之二元。此外,在白璧德看来,“二元论”还有新旧之分,“旧二元论”认为在人的内心存在善恶二元之对立,而以卢梭为代表的“新二元论”则在“人为”而“腐败”的社会与“自然”之间设立了一种对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性本善,“罪恶”是由外到内地带给人类的,因此犯罪的责任便轻而易举地交由社会来承担了。白璧德在《民主与领袖》一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卢梭的“新二元论”将善恶冲突从个人转移到了社会,这样一来,人之善恶不再由自己负责,而完全成了社会的责任。在白璧德这里,新旧两种“二元论”又构成了一组对立的“二元”,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白璧德的价值观与当时大行其道的“进化论”价值观相反,“新的”并不一定就是“真的”、“好的”,在他看来,内在于人的两种“自我”之间的对立才是“真二元论”(the true dualism),那么,何为“假二元论”,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外,白璧德的“二元论”还是一种“善恶二元论”,在此“二元论”不但构成了“内在制约”的基本内容及论说工具,更表现为一种鲜明的价值评断:“适度的法则”为善,走向“极端”为恶;“人文主义”为善,“人道主义”为恶;在一种“二元论”内部,“高上自我”为善,“卑下自我”为恶;在二种“二元论”之间,“旧二元论”为善,“新二元论”为恶。观点鲜明,不容混淆。从个人内心的“二元论”到个人与社会的“二元论”,从新旧“二元论”到真假“二元论”,似乎生活各个领域无不能够以“二元”来统摄说明。然而,白璧德在概括其“人文主义”人生观的时候却使用了存在的“三个等级”(three olders)这样一种陈述方式,。这三个等级分别为:宗教的(the religious)、人文主义的(the humanistic)和自然主义的(the naturalistic),下面将进一步疏解这个概念与“二元论”概念的联系。
3“存在的三个等级”(three orders ofbeing)
关于存在的“三个等级”,亦有几种类似的表述方式,分别见于以下各段引文。《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第一章中已频繁出现“人文主义”、“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存在的三个等级”所需的基本元素均已出现,但这些概念分别是作为对立的二元两两出现的,换言之,只构成了三组彼此联系的二元对立项,还未统合构成“存在的三个等级”。
在这个阶段,白璧德一方面批判过度的“自然主义”,另一方面亦批判过度的“超自然主义”,并引出了“人文主义”以协调二者,在这个结构中,不但“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作为两个极端彼此对立,“人文主义”之“适度的法则”亦与这两个极端各相对立,进行制约。当然,只有在“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走向极端”的时候,“人文主义”才呈现为一种制约力量,“走向极端”的“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恶”,均与“适度的法则”这一种“善”相对立,三者构成了对立的善恶二元,从而此时的“超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三种因素仍不过是构成了一种较为复杂的“二元”结构而已。
“存在的三个等级”这个概念首次明确见于《现代法国批评的大师们》一书,白璧德论及上个世纪的普遍谬误,是在于混淆了“存在的层级”(Planes of Being),这三个层级分为宗教的、人文主义的与自然主义的,中间虽然有无数的过渡阶段,但人仍可提升或降低至各个层级。
至《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存在的三个等级”出现另外一种表述方式:人“体验生命”可分为宗教的、人文主义的与自然主义的三个“层面”(three levels),。并且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三种元素几乎随处可见混合在一起,由于规模浩大的“自然神论运动”(the deisticmovement)。的推动,纯粹的“超自然主义”过渡到了纯粹的“自然主义”,这时神(God)与人(man)和自然(nature)便实际上融为一体了。
在白璧德的巅峰之作《民主与领袖》一书中,“存在的等级”换作了“人生观” (theview of life)一词,仍旧分为宗教、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三层。万变不离其宗。此书的第一章实际上全部根据这一观念而展开,并据此将政治思想分成了相应的三个类型。在《论创造性及其他》序言中,白璧德复论及帕斯卡所作的“三个等级”(the three orders)的区分,在此表述始发生一些变化,人生分为“物性自然”(material nature)、“精神”(mind)和“仁爱”(charity)三个等级。“仁爱”这个极富宗教意味的词汇指的自然是“神”或“宗教”层面,同时“精神”对应于“人”或“人文主义”层面, “物性自然”对应于“自然”或“自然主义”层面。此即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中第三个核心概念。
总之,“内在制约”概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二元论”概念的产生,而“存在的三个等级”则与“二元论”概念密切相关。这三个核心概念彼此联系,互相指涉,构成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而厘清这三个核心概念成为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的基础。例如白’德对“超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三者关系的理解,是如何从最初的较复杂的“二元”对立的形式,逐渐转化成为后来明晰的三层等级结构的,这种转化何以发生,其过程又是怎样,则是在阐明这三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以辨析的问题了。